
 〔文章加入收藏〕
〔文章加入收藏〕 

新介的故事,像是從時間的夾縫中誕生的。他站在 HIV 治療的轉折點上,既是見證者,也是參與者。他是台灣 HIV 長效針劑治療的第一批患者之一,在醫療歷史中,他的角色荒謬又真實——「HIV 治療長效針劑的大體老師」。
▸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:新介
▸ 確診年代:2018
在醫院的注射室裡,每次輪到他打針,總會有幾位護理師圍觀。「這個藥需要打在深層肌肉,推得太快會痛,針角度不對可能影響藥效……」有人低聲討論著,然後轉向他:「我們來試試新的手法,你不要緊張。」
他無奈地笑,「我大概是奇美醫院裡,讓最多人同時看過屁股的病人了吧?」
那像是一個 gay joke。
他把這些尷尬的瞬間說得幽默,但他心裡清楚,自己正站在醫療史的某個邊界。他的身體成了試驗場,他的經歷成了一頁教材。他不是醫師,卻成了治療的一部分。他不是革命者,卻活成了某種象徵。
但這一切的開始,卻是一場沉默的崩潰。

「那一次,我真的覺得自己完蛋了。」
1992 年生的新介,是在 26 歲生日前 2 天確診的。那天,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像是掉進了一個無聲的漩渦。然而又像是個意外的禮物。是毀滅,也是重生。
HIV 是突如其來的,但恐懼早已埋伏在生活的角落。他從年輕時就對健康異常警覺,每當發生高風險行為,便會主動篩檢,像是在為自己的人生設定安全網。但有一次,那張網破了,從篩檢的電話通知當中,他得知了自己的陽性身份。
更讓他無法接受的是,他並非因為疏忽而感染,而是遭受惡意傳染——有人在明知道自己有 HIV 的情況下,刻意隱瞞,與他發生「臨時拔套」的無防護性行為。當他察覺到異樣時,已經錯過了服用 PEP(暴露後預防性投藥)的黃金時間,唯一能做的,就是篩檢。並等待宣判。
確診後的那段時間,他的世界變成了一種無聲的黑白色。他陷入自我封閉,情緒像是一張無法平復的皺摺。他開始思考「如果一切都結束了會怎麼樣」,但他終究沒讓自己走上那條路。他的母親,在這場風暴裡,成了意外的燈塔。
「如果確診了,那就只能接受,不然怎麼辦?」他的母親這麼說,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討論晚餐吃什麼。
這句話沒有華麗的安慰,卻讓新介慢慢從恐懼裡走了出來。他開始思考:「如果我注定要與這個病毒共存,那麼我要怎麼活下去?」

新介開始服用「三恩美」,一種三合一的抗病毒藥物。服藥的前三個月,病毒就被壓制到了測不到的水平,醫師告訴他:「你的身體正在重新找回平衡。」但平衡並不意味著沒有波瀾,當藥效穩定後,副作用逐漸浮現。
「一開始只是偶爾噁心,後來變成吃東西就會反胃。後來改成吃素之後,聞到某些食物的味道,會想吐。」雖倒也不全然因為藥物的副作用,他撐了一段時間,最後還是向醫師求助,換成了「洛瓦梭」,副作用少了,但卻迎來另一個問題——體重快速上升。「我以前一直是瘦的,有一天家人突然說我變超胖,我整個被嚇到。」
體重的變化讓他開始在意自己的身體,開始懷疑這是否是藥物影響了新陳代謝。但他也清楚,這些藥物是讓他活下去的關鍵,沒有選擇的餘地。
「吃藥」這件事對新介而言一直都是種掙扎。不僅僅是因為 HIV,而是他過去的經歷所留下的痕跡。
「我本來就不喜歡吃藥,從以前看精神科的藥物開始就這樣,」他說,「以前治療精神疾病的時候,因為我常常不按時吃藥,結果治療就失敗了好幾次,後來還產生戒斷症狀,很不舒服。」這樣的經歷讓他對「每天吞藥」有一種本能的抗拒。
即便到了 HIV 治療,他還是習慣性地希望能有其他方式取代服藥。
因此,他始終一直有在關心治療的新聞,關心各種治療方式的藥物演變,也知道了長效針劑的治療方法正在各國進入初步的推廣階段——那是新的治療方式,不需要每天吃藥,兩個月打一針就好。於是,有天回診的時候,他主動向醫生詢問,然後醫生很開心地告訴他,疾管署開始把這項計劃納入健保了,問他,要不要嘗試看看?
「能少吃藥就少吃,這對我來說真的輕鬆多了——我本來就很討厭吃藥,當然是能少吃就少吃啊!」於是,他成了奇美醫院的第一批長效針劑患者,也成了「醫護訓練用的大體老師」。每次打針,護理師們總是成群結隊,先研究、再討論,最後輪流施打,像是在進行某種學術交流。
「我每次去打針,都覺得自己的屁股快要變成教材封面了。」
但說到底,他還是慶幸自己有這個機會。他不再需要每天服藥,生活變得更輕鬆自由。而最重要的是,他再也不覺得自己被這個病毒所束縛。

並不是每一次就醫經歷都這麼幽默。在某次因為急性腸胃炎掛急診時,他痛得幾乎站不住,家人帶他進醫院,他主動告知自己是 HIV 感染者,然後他發現,原本還算順暢的流程,瞬間變得停滯了。
後來來的病人,一個個被安排進病床,而他卻被晾在一旁。最讓他崩潰的是,當時已經病得連站都站不穩了,護理師不但沒有協助他爬上病床,卻在他自行爬上病床、不小心碰到護理師時,聽到護理師突然叫了一聲,跟一旁的另一個護理人員低語說:「啊!我碰到他了!」
這讓他後續碰到陌生的醫護人員,都有些戒心。
甚至,也曾清楚地聽見護理師在病房裡說:「小心幾號床是 H 款。」
「那一刻,我真的覺得自己不是病人,而是一個被標記的物件。」
這件事最後他選擇了投訴,但醫院的回應只是:「我們會加強教育訓練。」這讓他意識到,HIV 不只是一種疾病,它還是一種社會標籤,縈繞在人們的恐懼與誤解之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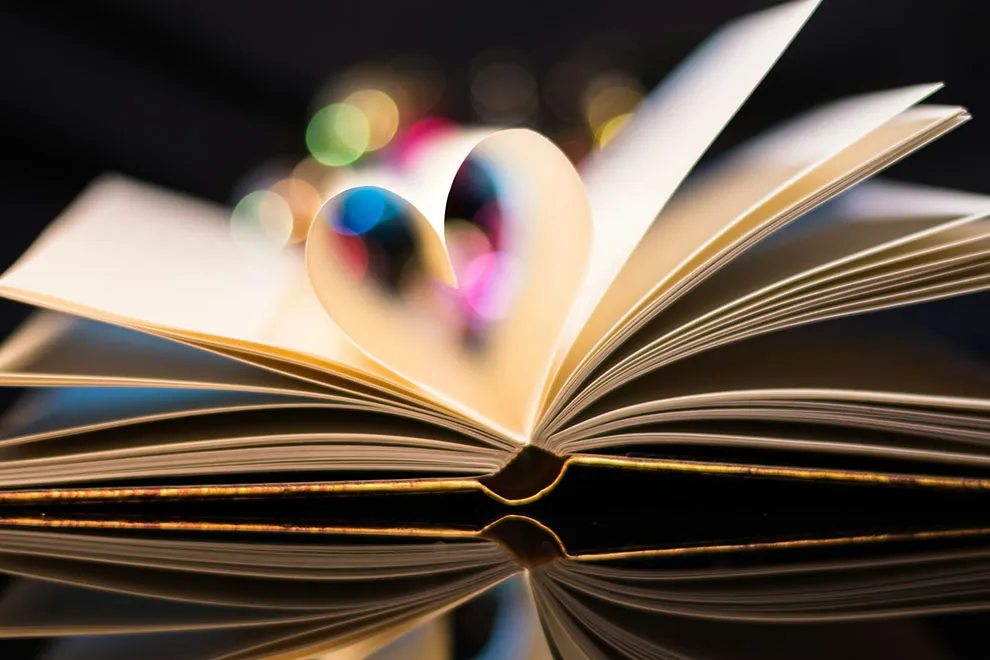
新介選擇站出來。他公開自己的經歷,加入 HIV 感染者社群,成為志工,參與倡議活動。他在網路上寫下自己的故事,告訴大家,HIV 並不可怕,真正可怕的是無知與偏見。
「我不覺得自己有生病。」他說,「HIV 對我的影響,遠不如社會對它的標籤來得嚴重。」
家人陸續得知他的狀況,有人接受,有人抗拒。
原本曾經因為同志身份的出櫃而離家的他,在另一群同住的家人之間,又再因為 HIV 的身份,得到了「特別」的眼光。有的長輩,曾經偷偷消毒他碰過的東西,要他「離小朋友遠一點」,但也有些長輩,始終給予他同等的關愛與包容。後來,那些介意,倒也隨著他一再、一再在社群平台上訴說自己的故事,轉貼HIV相關的文章與知識,他說,「長輩們雖然不會說,但我慢慢感受得到他們的改變與包容。」
所以他不後悔站出來,不後悔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他認為,如果 HIV 終有一天能夠被社會當作普通的慢性病來看待,那麼唯一的辦法,就是讓感染者站出來。
這是新介的故事。他從絕望中走出來,從噤聲中發聲,從恐懼中選擇幽默地活著。他的屁股或許已經被醫護人員們看過無數次,但他更希望有一天,這個社會不需要再用異樣的眼光來看待感染者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