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 〔文章加入收藏〕
〔文章加入收藏〕 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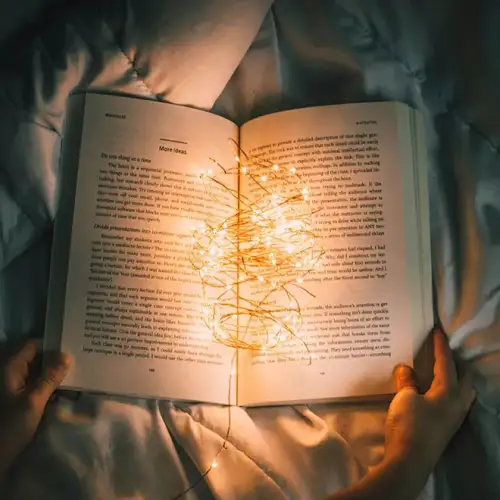
她的故事是一部橫跨數十年的長篇劇。是市場的喧囂、愛情的詐欺、醫療的風暴,以及頑強求生的韌性。她從量販店的促銷員開始,賣過腳踏車、清潔劑、蟑螂藥,甚至連橄欖油都賣了好幾年。
日復一日,她在賣場穿梭,與業務們混熟成一片。
2007 年的某一天,一個認識五、六年的業務對她說:「妳要不要結婚?」這句話在耳邊響起時,她沒想到,這不只是人生的轉折點,更是一場無聲的災難。「當時,我們會在一起,就是因為覺得應該可以結婚,應該可以有個未來。」Sandy 說著,語氣中帶著苦笑。但她不知道的是,這名男子早已有「N 個女朋友」。她投入得認真,卻換來一場欺騙。
▸ 歷史見證及受訪感染者:Sandy
▸ 確診年代:2007
她一直有定期捐血的習慣,從年輕時開始,維持體重讓自己符合捐血標準,幾乎是固定每兩、三個月就捲起袖子去捐一次。然而,某天她收到捐血中心的通知單,簡單幾行字,卻像是一顆炸彈:「請至衛生所報到。」
「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對勁,因為從來沒有被這樣通知過。我想說,一定是有什麼問題。」她回想起當時的心情,還是忍不住感嘆。「結果,真的有問題。」
衛生所的 HIV 確診通知,像是按下了一個巨大的開關,將她的世界一分為二——知道之前,與知道之後。她馬上聯想到那個「渣男」,他的背上長滿了一粒一粒的紅疹,當時她還天真地以為是喝酒、火氣大所導致,沒想到,真相是如此殘酷。
「當下打電話給他,我很大聲地罵他,你為什麼要害我?然後,我把電話掛掉,沒有等他說什麼。」這一掛,從此斷絕了聯繫。

確診後,她被轉介到昆明醫院,開始服用抗病毒藥物。但當時的藥物副作用極大,她吃了一次,頭暈目眩、全身無力,隔天完全起不了床,根本無法去上班。「我六歲開始,我媽媽就生病了,沒人照顧我。爸爸只要五個哥哥,我從小就知道一件事——我必須靠自己活下去。」於是,她選擇不吃藥。她不敢回診,因為治療影響到工作,而工作,是她唯一能夠掌控的人生。
這一停,就是 8、9 年的時間過去。她繼續在賣場工作,繼續被生活推著走,直到身體再也撐不住。
「2014 年的 11 月、12 月吧,那時候錢被朋友騙光,我自己也已經不吃不喝,根本沒想活了。結果,我真的就這樣倒下去了。」
她被送進醫院,住了一個禮拜,醫生開了藥,她又開始服藥。
但這時候的她,早已經病得太重,身體再也沒辦法承受過去的工作強度。她的家人,也沒有給她太多支持。「我那時候住院回家,我哥跟我說,妳什麼都不能吃。然後他真的每天只給我一碗白飯、一碗青菜。」
「我這樣撐了兩三個月,真的撐不下去了,就自己帶著換洗衣服,再次去醫院報到。」這一次,她住了 40 天,醫生說她的身體已經到了極限。「血打不進去,沒辦法輸營養,真的快不行了。」這一次,她終於徹底接受了醫療介入。

大病一場後,她的身體狀況不容許她獨立生活。這時,醫院的醫療團隊介入,轉介她到關愛之家,提供她額外的照護。她以前從來沒想過,自己有一天會住進這樣的地方,但當時的她,別無選擇。這個社會雖然有時對她殘忍,卻仍有一些系統運作著,將她撿了回來。
在關愛之家,她得到了穩定的照顧,身體狀況開始慢慢恢復。
有飯吃。睡得很飽。在山坡上的生活,安靜而沉穩。「每天吃飽睡,睡飽吃,還能看電視、唱卡拉OK,」她說。一兩個月一次吧?關愛之家的社工,帶著一群病友,以及感染 HIV 的孩子們,去電影院看電影,發一桶爆米花、一大杯可樂。熱熱鬧鬧的。那或許是她心中,生活對她少許的溫柔。
當她的狀況足以獨立生活,關愛之家則將她轉介到露德協會,協助她重返社會。
「我一開始也不知道露德協會是做什麼的,只知道那裡有人可以幫忙,幫我們找到一點方向。」她回憶著這段歷程,語氣平靜,但裡面藏著許多感慨。
命運一直捉弄她,讓她跌倒、受傷、被拋棄,但在最絕望的時候,體制仍發揮了一點作用,沒有讓她徹底掉落深淵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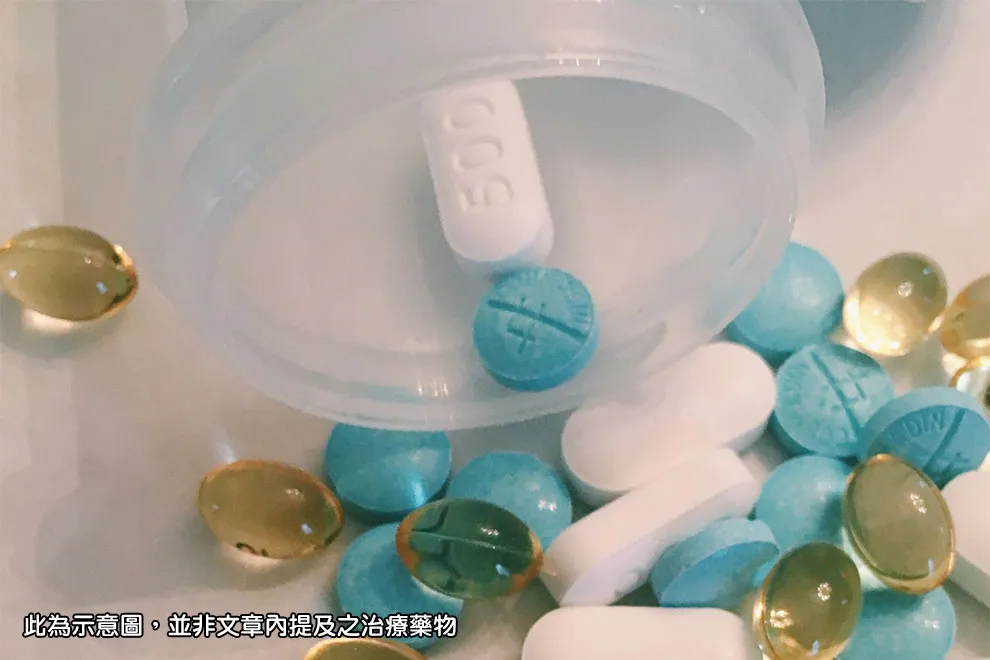
穩定接受治療後,在領取抗病毒藥物「三恩美」時,她通常還是去指定的醫院。但有一次——想到醫院在 2014 年住院時,在床尾掛上的「H」標記,她不想再回去那裡。於是試著在 Google 上搜尋看看有沒有其他藥局可以領。結果顯示,最近的指定藥局,竟然在好幾個行政區外的捷運站附近。
「太遠了。」她當時心裡嘀咕,但還是硬著頭皮跑了一趟。
她走進藥局,報上名字、拿出健保卡,等藥師輸入資料時,她心裡有點緊張。領到藥的那一刻,她突然有種說不出的不安。
「少一個人知道,就少一點麻煩。」她對自己說。
她快步離開藥局,回到街頭,等著過馬路時,卻開始後悔。她意識到,自己不應該來這裡領藥,不想在一個新的地方留下這個記錄。她害怕,如果這個藥袋上印著的名字被錯放在哪裡,被某個人看見,她的祕密會不會就此被洩露出去?
還是回指定醫院吧。
至少,在那裡,醫生、藥師早已經知道她的病歷,她不需要再擔心被誰「發現」。那一天,她坐上回程的捷運,緊緊抱著藥袋,心裡只慶幸了一件事——好險,這間藥局不在她住的地方,好險,這裡沒有認識她的人。

在外,她仍然不敢對大多數人坦承自己的身份。
「我家裡的人,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。我哥哥是在 2016 年、2017 年的時候發現的,他翻了我的藥盒,上網查了藥名,然後有一天跟我說:『妳以後不要再踏進我們家。』」
從那天開始,她不再回去弟弟的家。親情,徹底斷裂。
即便是在熟識的宗教團體中,她也選擇隱瞞,僅有極少數人知道她的情況。「有些人知道後,就開始跟我保持距離,坐得遠遠的,」她嘆了口氣,儘管社會對 HIV 的理解已經進步許多,但歧視依然存在。
但也是這些師姐,在她 2019 年因腎衰竭住院時,包了紅包給她,幫她付了看護費。
她現在還在調養身體,仍在學習如何在這個社會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她想再去工作,但也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無法承受高強度的勞動。她想學會拒絕,不再隨意借錢給不值得的人,也想學會更好地照顧自己。當年讓她感染 HIV 的男人,後來成了一名出家人。
「我七八年前在師父那邊看到他,他現在是個領眾的師父。」她沒有再跟他對話,沒有質問他,沒有要討回什麼。「我想,他看到我,應該會有一點愧疚吧。」
在訪談將近結束時,她看著露德協會的志工,忽然問道:「那什麼時候,我們可以一起去看電影、吃爆米花?」
眾人笑起來。
那一刻,她才發現,自己似乎很久沒有真正期待過什麼了。
這個念頭,讓她有點陌生,也讓她覺得,也許,真的能有一點點不一樣的未來。



